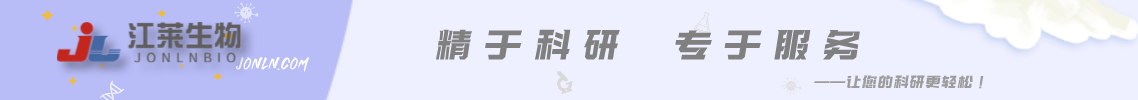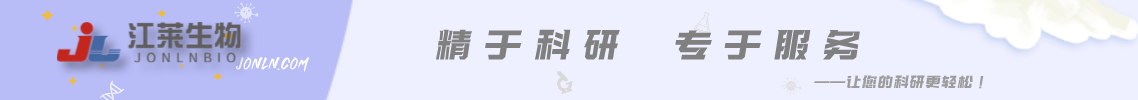究人員調查了來自世界各地的270名科學家,他們從事醫學,心理學,氣候變化和其它領域的研究。研究人員對科學家的調查是詢問一個簡單的問題:“關于今天的科學,如果你可以改變一件事,那么這件事是什么?為什么?”這些科學家包括了研究生、資深教授、實驗室負責人和領域里的專家。他們通過不同的方式告訴調查人員,科學家的職業正在被不恰當的激勵所綁架,其結果是損害科學。
科學研究的理想模式是高雅的。提出一個問題,建立一個客觀測試,并得到一個答案,再重復驗證。科學卻難于實現個理想。但哥白尼相信這一理想。登月火箭的科學家們也這么做了。
通常,科學家們從失敗的研究中吸取教訓。但失敗的研究可能導致職業生涯的終止。因此,在物質利益的誘惑下,便產生出陽性的研究結果以供發布。“發布或滅亡”,這句話幾乎影響著他們的每一個決定。這是一種揮之不去的魔咒,也像一條通往黑暗的絕路。
許多科學家已經受夠了。他們希望打破不正當的激勵和獎勵這一惡性循環。他們打算通過一段時間的反省,希望最終能夠推出更有效的科研管理機制。在我們的調查和訪談中,他們提供了多種多樣的想法,以改善科學研究的運行機制,使其更接近于理想的模式。
這個調查并非一個科學的民意調查。受訪者不成比例,他們僅僅來自于生物醫學、社會科學和說英語的社區。
問題一:學術界有巨大的經費問題
做任何研究,科學家都需要錢。實施研究,購置實驗室設備,支付他們的助理,甚至他們自己的工資。我們的調查對象告訴我們,獲得和維持資金是一個長期的障礙。他們抱怨的不只是資金數量,在許多領域,資金支持都在萎縮。還有科學研究資金的分配發放方式,迫使實驗室發表大量論文,從而滋生出利益沖突,并鼓勵科學家炒作自己的研究成果。
真正的新的研究需要更長的時間來工作,并且不總是有回報的。一個國家經濟研究局的工作文件發現,從整體上看,真正的非常規論文呈現出文獻引用較少的現象。所以,科學家和投資者都越來越遠離這些領域,更青睞那些周期短、可期待的高文獻引用方面的研究項目。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當獨立機構、政府和大學的資金來源枯竭時,科學家們可能會被迫轉向工業界或某些利益集團,并為集團的利益而積極的產出研究成果。例如,早前的很多營養科學的研究就是由食品行業資助的,這種與生俱來的利益沖突是不可避免的。同樣,絕大多數藥物臨床試驗由制藥公司資助。有研究發現,私人企業資助的研究更傾向于有利于贊助商的結論。
改善這些問題的一個簡單方法是政府簡單地增加可用于科學研究的貨幣總量。或者,更具爭議的是減少博士生人數。如果國會提高對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和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資助,降低一些對研究人員資助競爭的壓力。但那只是到此為止。資金將永遠是有限的,研究人員將永遠不會得到空白支票,以資助他們對科學項目的夢想。因此,改革是必需的。
一個建議:增強資金分配方案和程序的穩定性和可預見性。肯塔基大學神經生物學教授M. Paul Murphy寫到:“明確的解決辦法是簡單地使科學基金成為一個穩定的計劃,以每年的增長率在某種程度上與通貨膨脹掛鉤。”
另一個想法是改變資助方法:基金會和機構可以資助特定的人和實驗室一段時間,而不是某個研究建議項目。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已經這樣做了。這個方法會給科學家們更多的自由,去從事他們喜愛的科學研究與探索工作。
另外,最近研究人員在mBio雜志上呼吁建立彩票式資助系統。由計算機來測量申報項目的優劣,然后隨機確定受資助者。
問題二:許多研究設計不當
科學家們基本上是依據出版的標準來判斷自己的研究。發表文章的壓力促使科學家推出帶有瑕疵的研究結果,并將這些結果投送到著名的雜志。弗吉尼亞大學開放科學中心的Brian Nosek說:“令人驚訝的是,發表這類新穎研究結果的數量還大于其它種類的研究結果。”
這里的問題是,真正開創性突破的研究結果并不多見,這意味著科學家們面對壓力,為了自己的研究最終能夠具有那么一星半點“革命性”而展開博弈。這種現象在生物醫學和社會科學領域比較常見。這些偏見可以蔓延到研究決策:如早期是否隨機選擇參與者,設立對照組進行比較,或控制某一混雜因素而不是別的。
許多受訪者指出,不正當的激勵措施也可以促使科學家們在如何分析他們的研究數據時,采取“抄近路”的策略。亞利桑那大學的博士生Jess Kautz寫道:“當我完成對數據的分析,其結果看起來沒有足夠的重要意義時,那么我將承受令人難以置信的巨大壓力。相對于研究負責人企盼的良好研究結果而言,如果我得到了一個平庸的結果,那么這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壓力,足以讓他們可以將我掃地出門。此刻,這些問題盤旋在我的腦海里,它讓我懷疑自己是否還有能力對研究工作進行理性的、誠實的評估。”
如何修復不佳的研究設計?本次調查的受訪者提出了幾個關鍵的方法:鼓勵更強的研究設計,阻止對陽性結果的片面追逐,重建獎勵制度,確保研究過程的更加透明。
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社會心理學教授Simine Vazire 寫道:“我會依據研究方法的嚴謹性,而不是研究成果本身來抉擇獎勵。研究資助,出版物,就業,獎勵,甚至是媒體的報道,應更多基于研究設計和方法的優劣,而不是結果是否顯著、或是令人驚訝。”
多倫多大學心理學和神經科學教授MichaelInzlicht認為:“消除論文發表的偏倚是很重要的,應該通過問題的質量、研究方法的質量和分析的公正性來判斷論文的質量,而不是研究結果本身”。
(
將來商城www.abxsw.org)